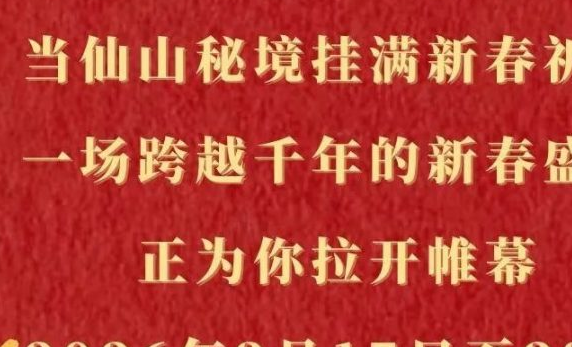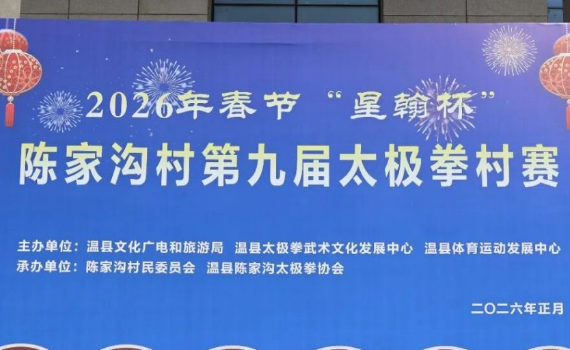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唐朝
今天,
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谈一谈唐代的历史或人物,
作为中国历史上和汉王朝并称的朝代,
我们似乎对唐代知之甚多:
雄才大略的君主、封侯拜相的名臣、
春风拂槛的美人以及讳莫如深的宫闱秘闻。
除了你我
明日即将到来的“马亲王”马老师
也不例外
今日
带你走进马伯庸的那些
“唐朝情结“
去看一看
他心中及笔下的唐朝

李白这一辈子,是真值了。
大部分古人,这一辈子连自己的家乡都走不出去,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稍微走得远一点,至于能机会遍游全国的人,凤毛麟角。
而李白一生,从二十五岁出蜀开始,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,去过的地方比许多现代人都多。这种人不去给快递或者物流做代言,真是可惜了。
李白诗里说“十五游神仙,仙游未曾歇”、“五岳寻仙不辞远,一生好入名山游”,真是一点都没夸张。当李白二十五岁的心情离开蜀中时,心情一定是无比的雀跃,所谓 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。兴奋之情,溢于言表。
而李白没什么具体工作,也没什么明确目的,他四处游历,两句诗就表达清楚了:“此行不为鲈鱼脍,自爱名山入剡中”。唐代的文人旅游风气很兴盛,他们四处干谒投献,结交官员,刷声望值。没有什么KPI考核任务——悠游闲逛,没有日程,这才是旅游的心境。李白的好基友杜甫说“九州道路无豺虎,远行不劳吉日出”,说明盛唐之时,社会治安尚好,也不用担心安全。
于是李白便玩的很疯,哪怕是他从长安黯然离开后的低谷时期,也没闲着。
特地跑到东鲁去郁闷,还顺手写出了“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这样的句子,给自己打气。写完以后,李白笔一扔,又跑吴越玩去了。所以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还有另外一个题目,叫做《别东鲁诸公》。

说回正题。我一直有一个猜想。李白的诗如此豪放飘逸、想象奇绝,一定是和他的丰富游历分不开的。
李白之所以写出那么多汪洋肆恣的想象力杰作,不仅是因为旅行能涨经验值,也因为旅行提供了足够多的空闲时间。
唐代交通要么靠腿,要么靠牲口或船,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赶路上。那时候没随身听,也没手机电子书,那么长的时间,一个人干坐着实在太无聊了。那么打发时间最好最方便的方式,就是开脑洞。
以李白的才华,再加上这么多空闲脑洞时间,能碰撞出何等杰作的作品,不问可知。他的几首开脑洞的名作,比如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、“云山海上出,人物镜中来”、“兴酣落笔摇五岳,诗成笑傲凌沧州”、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”等等,皆是旅途中触景生情,随手演出瑰丽大气。就连做梦,都是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这种级别的。
李白有一首《游泰山六首之一》,特别能说明他这个习惯:“登高望蓬瀛,想象金银台。天门一长啸,万里清风来。玉女四五人,飘飖下九垓。含笑引素手,遗我流霞杯。稽首再拜之,自愧非仙才。旷然小宇宙,弃世何悠哉。”
只是一次普通的登高而已啊,杜甫、陈子昂最多感慨一下人生历史,可人家李白往那一站,从“想象黄金台”开始,二话不说,立刻进入疯狂脑补模式,想象力就如同过节放花似的,噼里啪啦往外炸,生生造出一部玄幻大片的场面来。可见李白的脑洞,开得真是随时随地,到后来已成为习惯了。
这随走随爆脑洞的风格,伴随了李白终生。有人说,李白可以算作是中国最早的快递员,跑遍全国,不送包裹,只送脑洞,准时送达,而且保质保量,每一个,都是黑洞级别的好货色。他就是他自己诗里的那只菜鸟:“青鸟海上来,今朝发何处,口衔云锦字,与我忽飞去”。游遍全国,把自己的脑洞送去千家万户,让每一个人都能共享其宏大飘逸之美。
节选自
《李白、旅行和脑洞》

杜甫有一首诗,叫做《寄赞上人》,是写给好盆友赞公和尚的。这首诗的背景,是杜甫在秦州西枝村想买套山间茅屋,于是和尚陪着他到处转悠看房。可杜甫很挑剔,左看不合适,右看不趁心,最后没买着。后来杜甫听说附近有个叫西谷的地方不错,就给赞公和尚写了这首诗,邀请他再陪自己看房。
在这首诗里,杜甫先说自己“年侵腰脚衰,未便阴崖秋”,年纪大了,腿脚不灵便,不适合住在背阴的悬崖旁边,然后表示“近闻西枝西,有谷杉黍稠。亭午颇和暖,石田又足收”,是个向阳的好去处,值得去看看。
那么什么时候去呢?杜甫给了个日子——“当期塞雨干,宿昔齿疾瘳”,等到不下雨路面都干透、我牙疼的老毛病不再发作的时候吧。
原来杜甫一直就在闹牙疼,一疼起来,根本没心思看房。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,杜甫并没在秦州置业,而是跑到了成都弄了一个草堂。
杜甫这牙疼,还不算严重,所以他只是在诗里捎带着提了一句,没有多做发挥。而另外一位大诗人白居易的遭遇,可就比他惨多了。
白居易是个乐天现充,可即使这样的人,碰到牙疼都发蔫儿。他有一首诗,叫做《病中赠南邻觅酒》,写的真是情真意切:
头痛牙疼三日卧,妻看煎药婢来扶。
今朝似校抬头语,先问南邻有酒无?
在白乐天的诗里,这首很一般,。但那种绝望的感受,却是从直白的字里行间喷薄欲出。牙疼得足足在床上躺了三天,站都站不起来,最后实在忍不住了,不得不找邻居借点酒来,说不定能醉杀牙神经止止痛,最不济也也能让人醉过去,暂且忘却疼痛。
白居易的牙齿毛病,比杜甫严重,所以感受也格外地深切。他后来年纪大了,牙齿脱落,还特意写了一首《齿落辞》。写得实在太好,不得不全文照录,以飨同病:
嗟嗟乎双齿,自吾有之尔
俾尔嚼肉咀蔬,衔杯漱水;
丰吾肤革,滋吾血髓;
从幼逮老,勤亦至矣。
幸有辅车,非无龂齶。
胡然舍我,一旦双落。
齿虽无情,吾岂无情。
老与齿别,齿随涕零。
我老日来,尔去不回。
嗟嗟乎双齿,孰谓而来哉,
孰谓而去哉?齿不能言,请以意宣。
为口中之物,忽乎六十余年。
昔君之壮也,血刚齿坚;
今君之老矣,血衰齿寒。
辅车龂齶,日削月朘。
上参差而下卼臲,曾何足以少安。
嘻,君其听哉:
女长辞姥,臣老辞主。
发衰辞头,叶枯辞树。
物无细大,功成者去。
君何嗟嗟,独不闻诸道经:我身非我有也,
盖天地之委形;君何嗟嗟,
又不闻诸佛说:是身如浮云,
须臾变灭。由是而言,君何有焉?
所宜委百骸而顺万化,
胡为乎嗟嗟于一牙一齿之间。
吾应曰:吾过矣,尔之言然。
白居易写得好,那是因为有生活。有人比他写得更好,说明那个人的牙病比白居易还严重。这人大家也熟,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。
韩愈写过一首《落齿》:
去年落一牙,今年落一齿。
俄然落六七,落势殊未已。
馀存皆动摇,尽落应始止。
忆初落一时,但念豁可耻。
及至落二三,始忧衰即死。
每一将落时,懔懔恒在已。
叉牙妨食物,颠倒怯漱水。
终焉舍我落,意与崩山比。
今来落既熟,见落空相似。
馀存二十馀,次第知落矣。
倘常岁一落,自足支两纪;
如其落并空,与渐亦同指。
人言齿之落,寿命理难恃,
我言生有涯,长短俱死尔。
人言齿之豁,左右惊谛视,
我言庄周云:木雁各有喜。
语讹默固好,嚼废软还美,
因歌遂成诗,时用诧妻子。
这首诗写得很诙谐,也很苦涩。
大唐的牙病受害者里,除了杜甫、白居易、韩愈几位大家之外,还有一位倒霉孩子,值得单独说说。
这个人名气不如前面几位大,叫宋之问,初唐著名诗人。这个人对律诗贡献良多,比较著名的一首是《渡汉江》:“岭外音书断,经冬复历春。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。” 但他干的最出名的一件事,是发现自己外甥刘希夷写了两句诗: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,惊为天人。宋之问跟刘希夷说这诗我很喜欢,反正别人也不知道,要不你把版权送给我吧?刘希夷不干,宋之问把脸一翻,把装满沙土的袋子,活活把自己外甥给压死了……
这么一位才华出众、人品低劣的诗人,在武周一朝时,曾经给武则天献上一首《明河篇》,求个北门学士的头衔。不过武则天根本不予理睬,崔融觉得挺奇怪,问她:“《明河篇》写的挺有才呀,您干嘛不见他?”
武则天回答:“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,但以其有口过。” 口过就是口臭的委婉说法。原来宋之问有严重的牙病,导致口气恶臭,武则天一闻就头疼。消息传出宫去,把宋之文羞愧得不成,“终身渐愤”。虽然他后来混出了头,以五品学士扈从武后朝会游豫,以巧思文华得宠,风光无二,可这个“口过”的耻辱,跟随了他一辈子。
节选自
《古代那些牙疼的倒霉孩子》
晚唐有一位不太著名的诗人,叫于濆。
“濆”字是个多音字,念分的时候,指水边;念喷的时候,指水花涌起。古人讲究名、字相配,两者之间要有一定联系。于濆的字叫子漪,漪指水波向四周泛开。一个漪字是水横着动,一个濆字是水竖着动,正好相配。所以于濆应该是念作于喷。
于濆人如其名,确实挺能喷的。
他是邢台人,游历于京师,并在咸通二年得了进士及第。不过于濆并未得到重用,最高只做到泗州判官。少年天才,游历京师,进士及第,不为重用,郁郁而终……简直就是标准的唐代诗人履历。
在当时,社会上流行靡绮浮艳的格调,大多数人精研格律,沉迷于小确幸和艳体,不怎么接地气。于濆最看不上这种玩意儿,坚持走现实主义路线。他认为诗的使命是矫弊俗、揭虚伪,而不是风花雪月。
于濆师法于杜甫,学其沉郁顿挫;师势于孟郊,学其五言刻琢;师术于白居易,学其浅白直切。三位大家融汇一处,再加上“矫弊俗”的创作追求,铸成了于濆的独有风格。
他最著名的一首诗,叫做《古宴曲》,是这样写的:
雉扇合蓬莱,朝车回紫陌。
重门集嘶马,言宴金张宅。
燕娥奉卮酒,低鬟若无力。
十户手胼胝,凤凰钗一只。
高楼齐下视,日照罗衣色。
笑指负薪人,不信生中国。

笑指负薪人,不信生中国
一群达官贵人,站在高楼之上,端着酒杯谈笑着,忽然看到楼下走过背着柴薪艰难行进的樵夫,议论纷纷,根本不相信还有这样的穷人。
这种写法,立刻会让人想起张俞那两句著名的“遍身罗绮者,不是养蚕人“。不过张俞的作法,是以衣衫为载体,对比富贵人与养蚕者穿着,视角始终放在养蚕人的情绪上。
于濆既然叫于喷,比张俞要更主动。他并未去探究负薪者的状态,在他看来,这是不言自明的,反倒是那一群高高在上轻言笑语的人,太值得写写了。
“笑指“、”不信“二字,嘴脸跃然纸上。笑指,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,只当是个酒后的段子;不信,是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,根本不存在什么苦处和煎熬,他们天真地惊叹,天哪在大唐盛世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生活?
这种状态,比杜甫的《石壕吏》、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更令人感到郁闷。对于高楼之上的这些人来说,自有石壕吏和黄衣使者在一线去欺凌弱者、剥削贫者、不劳亲自动手。久而久之,在他们眼里,这些底层劳动者的存在感,比一个酒席段子多不了多少。那些穷人的喜怒哀乐,也就成了远远传来的杂音,远不及丝竹悦耳。
无视的笑,比穷凶极恶还是可怕。
所以他们不信,拒绝相信这种现实;所以他们笑指,对那个群体漠不关心。负薪者也罢、卖炭翁也罢、养蚕人也罢,无论他们遭遇什么,对高楼之上的人来说都只是谈资罢了。他们不理解石壕村的老翁为什么逃避兵役?不明白卖炭翁卖光了炭有什么好伤心的?那些砍柴的,干嘛扛着柴火弄脏街道?养蚕的,为啥穿的那么破影响市容?杜甫非要住廉价破茅屋,怎么不住广厦?饥荒年代,大家为啥不吃肉糜?
这都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,也是诗人想要我们理解的。
于濆,其实不算喷,京城居易,其实真居不易。千载之下,看到这样的诗句,仍旧会让人震撼。
节选自
《笑指负薪人,不信生中国》